勾引 处男 子居:清华简十四《两中》剖判(一) | 中国先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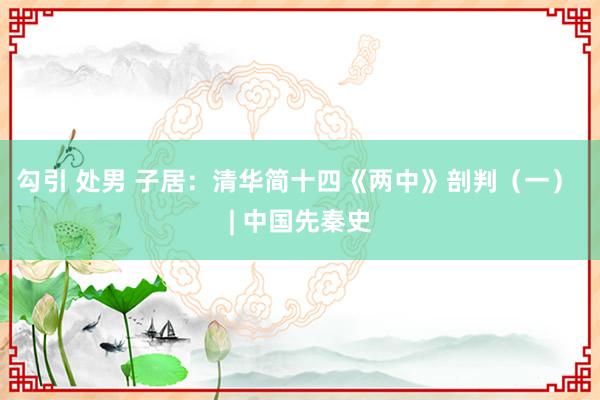
清华简十四《两中》剖判(一)勾引 处男
子居
整理者在证明部分言:“本篇共八十八支简(缺失一支,实存八十七支),简长约四十五·八厘米,宽约〇·五厘米,三说念编,简背有刻割印迹。无篇题,简文主体为两中(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故据以命篇。本篇竹书据竹简形制分为六个编联组,分别是简一至十八、简十九至二十九、简三十至四十二、简四十三至六十三、简六十四至六十九、简七十至八十八。简文以夏朝初定为布景,夏启向两中究诘书读五车之说念,两中指出要秉持中说念,依从五章,着力九德,鉴戒天则来贬责国度,沟通夏启恪行德祀,治狱行政,四时行事,要幸免邦家初定后的各样不妥行动,并言及夏启取代伯益的历史。本篇的拟托手法、结构和内容等都与清华简第十二辑的《参不韦》近似,二者不错合不雅。简文触及夏朝初期的历史神话、上古政事念念想等内容,是一篇首要的先秦佚籍。”[1]整理者的编联大体可从,不外还略有值得存疑的场地,第一,简8拼合后远较其它各简为短,残断处高下也不吻合,之后说“皆来会繁,而格于玄天”也显然不行包括“皇天天主”在内,推断当是简8a下端“天主”与简8b上端“山川”之间还有缺失的一段十二字支配简文。第二,简38上端为“仲又言曰”,以篇内行文例,称“又言曰”的情况,前边皆是“圭中”或“祥中”,因此简38之前应该至少还有一支佚简,该佚简下端末字应该是“圭”或“祥”。笔者《清华简十二《参不韦》剖判(一)》[2]中已言:“《参不韦》篇的内容沿路为参不韦对夏后启的片面训告,因此《参不韦》篇当可归于《书》类文件中的《夏书》。换用笔者在《先秦文件分期分域连系之三 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上)》[3]一文中所建立的派系分类判断模范进行分析也不难获知,《参不韦》篇是《书》类文件中与《逸周书》较接近的广义书家文件,且《参不韦》有着显豁的阴阳家、皆说念家倾向,何况八成是当今通盘可见文件中最早的皆说念家倾向文件。篇中强调的'刑’仍是接近于法家的'法’不雅念,但其以天说念妖祥凶殃彰显处罚则尚未脱离原始的宗教意志,因此从这个角度同样不错推断其成文时期约莫在管仲派系成型之前,也即在春秋前期时段。”在《清华简十二〈参不韦〉剖判(三)》[4]还提到:“探究到皆东说念主不祖夏禹或夏启,因此多情理推断清华简《参不韦》篇是杞东说念主东迁后与皆东说念主文化交流会通的产品。……杞国与皆国的走动密切盖即始于皆桓公时期,鲁僖公十四年为公元前646年,属春秋前期后段,正可与笔者前文剖判内容分析清华简《参不韦》篇主体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段、末段之际投合。”这也同样是《两中》的成文时期上限和前三分之一内容的作风特征。自“圭中又言曰:后惟狱时疏”开动,《两中》的文风与内容就发生了改换,这也恰是篇中开动以“两”代称“祥中”的段落,是以自此往后应该都是杞国一火国后《两中》篇流入他国,后东说念主一再补充加入的内容。从“中又言曰”至“其复加之福”这一部分出现了篇中其它部分未见的虚词“斯”,因此这个包括了四季的部分原应该是单独成篇的。此后原各有起源的段落可推断约莫为,自“圭中又言曰:后,余方告女,天建天训”至“其命不成”,自“中曰民卣狂残”至“后其啻”,自“圭中又言曰:邦家”至篇末的“则可加型”。临了的这部分,“於民省略”句出现了单用的虚词“於”,是以可推知这部分红文时期最晚,仍是晚至战国后期,而全篇都莫得出现虚词“乎”则证明该篇的临了整理成篇时期很可能当早于战国后期后段,也即早于《五纪》,因此《五纪》篇内的干系内容应该很大可能性是受《两中》的影响。
勾引 处男
【宽式释文】
夏后奠卣,庶灵因固,九德溥扬,两中乃入,格于有河。三年,在日乙丑,两中又降,格于有夏。教劼皇帝,敷纶天律,乃后斗亥。
启乃宾逆天好意思,成斋三日,乃善大备,敷设惟则,黄收玄衮、朱裳素带、并幅緆藻二十,玄韍麃舄以崇,就位于会门之左,
珪中乃进,左执玄珪,右执玄戉,以宾于后所。祥中乃进,左执瑞,右执黄鈇,以从珪中。
【释文剖判】
图片
(夏)后奠卣(攸)〔一〕,庶霝(灵)因固〔二〕,九悳(德)尃(溥)昜(扬)〔三〕。整理者注〔一〕:“《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皇帝位,南面朝世界,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奠,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峻岭大川。」卣,读为「攸」。《说文》:「攸,行水也。」或从水,从支。段玉裁注:「水之安行动攸,故凡可安为攸。」此处「攸」正用本义,「奠攸」指夏禹「奠峻岭大川」,治水到手。一说「卣」读为「修」,整治。”[5]“夏后”不行专指“禹”,因此整理者注“卣,读为「攸」。《说文》:「攸,行水也。」或从水,从支。段玉裁注:「水之安行动攸,故凡可安为攸。」此处「攸」正用本义”当非是。“夏后定卣”是原因,“庶灵因固”是效果,因此可推断“卣”是指的与祭祀干系的内容,《周礼·春官·鬯东说念主》:“鬯东说念主掌共秬鬯而饰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门用瓢赍,庙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丧之大渳,设斗,共其衅鬯。凡王之皆事,共其秬鬯。”郑玄注:“祼,当为'埋’字之误。也。故书'蜃’或为'谟’。杜子春云:'谟当为蜃,书亦或为蜃,蜃,水中蜃也。’郑司农云:'脩、谟、概、散,皆器名。’玄谓庙用脩者,谓始禘时,自馈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读曰'卣’,卣,中尊,谓献象之属。尊者彝为上,罍为下。”贾公彦疏:“郑破祼为埋者,若祼则用郁,当用彝尊,分歧在此而用概尊,故破从埋也。埋,谓祭山林。则山川用蜃者,大山川。'司农云脩、谟、概、散,皆器名’者,先郑从古云谟,后郑亦不从之矣。'玄谓庙用脩者,谓始禘时’者,谓练祭后迁庙时。以其宗庙之祭,从自始死已来无祭,今为迁庙,以新死者木主入庙,特为此祭,故云始禘时也。以三年丧毕,来岁春禘为终禘,故云始也。云“自馈食始”者,皇帝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践、馈献,乃有馈食进黍稷。医师士礼无馈献已前事,直有馈食始,即《特牲》、《少年》皆云馈食之礼是也。今以丧中为吉,祭不可与吉时同,故略同医师士礼。且案《巨额伯》,宗庙六享,皆以祼为始,当在郁入用彝,今无须郁,在鬯东说念主用卣尊,故知略用馈食始也。……郑以脩从卣者,《诗》与《尚书》及《尔雅》皆为卣,脩字于尊义无所取,故从卣也。云'卣,中尊,谓献象之属’者,案下《司尊彝》职云:'春祠夏礿,祼用鸡彝、鸟彝,朝践用两献尊,馈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为上,罍为下,献象之属在其中,故云中尊献象之属。更云'彝为上,罍为下’者,欲推出卣为中尊之意也。”《尔雅·释器》:“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郭璞注:“皆盛酒尊,彝其总名。”邢昺疏:“别酒尊大小之异名也。彝其总名。彝者,法也,与诸尊为法。《司尊彝》云:'鸡彝、鸟彝、斚彝、黄彝、虎彝、蜼彝。’是也。卣者,下云'卣,中尊也。’孙炎云:'尊彝为上,罍为下,卣居中。’郭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彝之间,即《周礼》牺象壶着太山等六尊。’是也。……彝、卣、罍三者皆为盛酒器也。”郝懿行《义疏》:“器者,当篇之总名,独于此言器者,尊彝,礼器莫尚,故独擅器名也。彝者,《说文》云:'宗庙常器也’。《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将果读爲裸。’六彝者,鸡彝、鸟彝、犟彝、黄彝、虎彝、雎彝也。《序官·司尊彝》注:'郁鬯曰彝。’贾疏云:'同是酒器,但盛郁鬯与酒不同,故异其名。’关联词尊彝,裸神之器,故专器名。《明堂位》正义云:'彝,法也,与余尊为法,故称彝’,是其义也。卣者,《诗》:'秬鬯一卣’,毛传:'卣,器。’《左氏·僖廿八年》正义引李巡曰:'卣,鬯之器也。’关联词卣亦鬯器,以非裸时所用,故次于彝。《鬯东说念主》云'庙用修。’郑注:'脩读曰卣。卣,中尊,谓献象之属。’《司尊彝》释文:'卣,本亦作攸。’关联词'攸’与'脩’皆'卣’之通借矣。”是其说以“卣亦鬯器,以非裸时所用,故次于彝。”但是先秦文件凡言“鬯”皆是用“卣”,未见以“彝”的情况,《尚书·洪范》所附《分器序》:“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颖达疏:“《周礼》有司尊彝之官,郑云:'彝亦尊也。郁鬯曰彝。彝,法也,言为尊之法正。’关联词盛鬯者为彝,盛酒者为尊,皆祭宗庙之酒器也。”所言“盛鬯者为彝”,那么则是“卣”即可称“彝”,因此《尔雅》所言“卣,中尊也”导致的孙炎所说“卣居中”盖非是。“卣”是祭器,用来盛鬯,而祭祀用鬯,是一种极限的特权,《周礼·春官·鬯东说念主》:“凡王吊临,共介鬯。”郑玄注:“郑司农云:'鬯,香草,王行吊丧被之,故曰介。’玄谓《曲礼》曰:'挚,皇帝鬯。’王至尊,介为执致之,以礼于鬼神与?《檀弓》曰:'临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适四方,舍诸侯祖庙,祝告其神之辞,介于是进鬯。”贾公彦疏:“司农云'鬯,香草’者,见《王度记》云'皇帝以鬯,诸侯以薰’,《礼纬》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真的秬鬯,无香草,故后郑不从也。云'王行吊丧被之,故曰介’者,先郑之意,以介为被,似若《春秋》被练之义,故云被之。后郑亦不从。'玄谓《曲礼》曰’者,《下曲礼》文。云'挚,皇帝鬯’者,彼挚下与皇帝鬯、诸侯圭卿羔已下为目,此皇帝以鬯为挚,若卿羔之类。但皇帝至尊,不自执,使介为执致之。'以礼于鬼神与’者,无正文,盖置于神前,故云'与’以疑之。”《礼记·曲礼》:“凡挚,皇帝鬯,诸侯圭,卿羔,医师雁,士雉,庶东说念主之挚匹。”《礼记·表记》:“皇帝亲耕,粢盛秬鬯以事天主,故诸侯勤以辅事于皇帝。”《国语·周语上》:“及期,郁东说念主荐鬯,牺东说念主荐醴,王祼鬯,飨醴乃行,百吏平民毕从。”相关于此,诸侯若想用鬯则要仰赖于王,《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皇帝。”也即是说诸侯淌若莫得获赐圭瓒则也没条款用鬯。皇帝祭祀用鬯势必要以“卣”,而“奠”字的本义据《说文·丌部》:“奠,置祭也。”《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奠:定也,荐也,置祭也,顿爵神前也。”以此“奠卣”当然也就有了和“定鼎”近似的文化属性,《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而因为赢得相应的祭祀,众神灵当然也就舒心了,是以有“庶灵因固”。
整理者注〔二〕:“庶灵,众神。固,安稳。”[6]“庶灵”犹先秦文件所言“诸神”,最早可见于《墨子·非攻下》所转引的《书》系佚文:“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西周金文未见“固”字用例,《国语·晋语二》:“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韦昭注:“固,定也。”是以“因固”犹言“以定”。《史记·孔子世家》:“山川之神足以法纪世界,其守为神。”《集解》:“王肃曰: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是以天主除外的诸神在东说念主间的代表即诸侯,“庶灵因固”骨子上指的也即诸侯安稳。
整理者注〔三〕:“九德,九种优良品格。《书·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东说念主有德,乃言曰载釆釆。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羲,彰厥有常,吉哉!」清华简《说命下》简八:「昔在大戊,克慎五祀,天章之用九德,弗易平民。」尃,读为「溥」,《说文》:「大也。」《诗·公刘》「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毛传:「溥,大。」”[7]笔者在《清华简〈说命〉下篇剖判》[8]已言:“'九德’之称,不见于巨贾、西周时期,而始见于约为春秋前期的《尚书·立政》:'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后来《山海经·西山经》'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亦有称,再后则有《国语·周语下》:'是以宣养六气、九德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是皆泛称而未具体证明。至于《逸周书》的《文政》篇言:'九德:一忠,二慈,三禄,四赏,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资,七祗民之死,八无夺农,九足民之财。’《宝典》言:'九德: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乃不崩,三慈惠,知老小,知老小,乐养老,四忠恕,是谓四仪,风言大极,意定不移,五中正,是谓权断,补损知选,六恭逊,是谓容德,以法从权,安上无慝,七宽弘,是谓宽宇,准德以义,乐获纯嘏,八温直,是谓明德,喜怒不郄,主东说念主乃服,九兼武,是谓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经。九德广备,次世有声。’《常训》言:'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忘我曰类,辅导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舍短取长之曰比,经纬寰宇曰文,九德不愆,劳动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管子·水地》:'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洁宽厚,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明后,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东说念主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所言又都不同样。因此可知,'九德’之说当起自春秋前期,本无确解,故诸书各执一词。”是以这也就决定了《两中》篇的成文时期不会早于春秋前期。
两中乃内(入)〔四〕,
图片
(格)于又(有)河〔五〕。整理者注〔四〕:“两中,即下文之「圭中」和「祥中」,又称「天中」,旧书未见,为天帝之使臣。”[9]而整理者在简30注一六言:“圭中言毕,后多为祥中搪塞,「两乃应之」之「两」疑即祥中之异称。”[10]且在简38注三五言:“中,「圭中」之省称。”[11]那么何故此处的“两中”整理者莫得评释成动作“祥中之异称”的“两”和“「圭中」之省称”的“中”合并成的称谓呢?不知整理者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持何种不雅点。“乃”为语助词,《礼记·杂记》:“祝称卜葬虞,子孙曰'哀’,夫曰'乃’。”孔颖达疏:“乃者,言之助也。”篇中“乃”字多为这一用法。“乃入”于先秦传世文件最早可见于《大戴礼记·诸侯迁庙》:“祝导奉衣服者乃入,君从奉衣服者初学左,在位者皆辟也。”《诸侯迁庙》中使用了虚词“焉”、“者”,因此可知成文时期当不早于春秋前期,这正可印证《两中》篇的成文时期也不早于春秋前期。
整理者注〔五〕:“
图片
,读为「格」。《仪礼·士冠礼》「孝友时格,永乃保之」,郑注:「格,至也。」有河,为古部族。有,名词词头。清华简《保训》简八:「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12]“格于”某地,先秦文件沿路见于《书》系文件,战国时期未见用例,因此可知前三分之一的这部分《两中》其成文时期当不晚于春秋末期。“有河”当是地名,《逸周书·度邑》:“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很显然《度邑》中的“有河”就不是“古部族”,整理者所引《保训》“假中于河”也并未称“有河”,而仅是称“河”,以此启事将“有河”与“河”浅薄等同并觉得皆是“古部族”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何况,前文既言“夏后奠卣”,那么“两中乃入”当然是为了承认夏后氏的政权为天命所授,这种情况下淌若“两中”入的“有河”是夏后氏除外的“古部族”,不就等于胜仗抵赖了夏后氏的政权正当性而形成了“有河”这个“古部族”才是天命所归,这显然是分歧理的,是以整理者注以“有河,为古部族”当非是。这里的“有河”,应该即是大禹治水后所居都城的所在地。《毛诗·桧风·匪风》:“顾瞻周说念,中心怛兮。”毛传:“转头曰顾。”周武王转头就会看到的“有河”当然指的是洛阳北部的黄河河段,那么“两中乃入”的“有河”不难判断即在近邻。《孟子·万章上》:“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固然《续汉书·郡国志》:“阳城,有嵩峻岭,洧水﹑颍水出。”注引《汲冢书》:“禹都阳城。”但这显豁是以阳翟为阳城,《汉书·地舆志·颍川县》:“阳翟,夏禹国。”颜师古注:“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王先谦《补注》:“《颖水注》:'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金鹗云:'禹都有二。始都阳城,即避舜子处,以为都;后都晋阳,乃从尧舜所居之方。’服虔《左传》注云:'尧居冀州,虞夏因之。’《郑诗谱》云:'魏国,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与唐近,同在河北冀州,故祝鮀云:'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于殷虚,启以商政’,则禹都即唐国。杜注:'今太原晋阳是也。’《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都’,而曰'夏禹国’,知禹不都阳翟矣。先谦案,金说与说念元夏禹始封于此之文彼此印证,足以发明班旨。惟《涑水注》,不妥云安邑夏都,为皇甫谧之说所乱,亦爱博之过也。刘昭直云:'阳翟,禹所都’,误矣。”可见阳翟仅仅相传为帝舜时禹所受的封地,并非帝舜牺牲之后夏禹的都城。由《两中》开篇所言“两中乃入,格于有河”来看,此“阳城”实当为“河阳”,《春秋·僖公五年》:“天王狩于河阳。”杜预注:“晋地,今河内有河阳县。”《水经注·河水五》:“河水又东,迳河阳县故城南。《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郭颁《世语》曰:'晋文王之世,大鱼见孟津,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论衡》曰:'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云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燌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昔禹治激流,不雅于河,见白面长东说念主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所谓“白面长东说念主鱼身”、“白鱼入于舟”所说当然是白鲟,“大鱼见孟津,长数百步”也当是鲟鱼,而“禹治激流,不雅于河”得河图于孟津也标明禹治水的主模范域即是孟津地区。《史记·赵世家》:“反高平、根柔於魏。”《集解》:“徐广曰:《编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阳曰河雍,向曰高平。”是《竹书编年》可证河阳会简称“阳”,当然也就可称“阳城”。河阳一带可与这一情况对应的考古古迹有东杨村古迹和留庄古迹,据《河南洛阳祯祥东杨村古迹》:“东杨村古迹位于洛阳祯祥公社东杨村南,它北倚太行山支脉(当地巨匠称之为北邙山),南距黄河约3公里。这一带地势北高南低,通盘古迹被冲积土所袪除。经铲探,在古迹近邻发现一条故河说念,由东向西又拐向南,古迹正坐落在河湾处,总面积约16万经常米。……东杨村一期文化与洛阳锉李二期、郑州𤰙𤰚王古迹的河南龙山文化,当属于归并文化期的遗存,颠倒于河南山文化的中期。……东杨村二期文化属于临汝煤山古迹第一期文化,颠倒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东杨村三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第四期)当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13]《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留庄古迹:新石器期间至青铜期间古迹。位于河南省济源市东南。面积8万经常米。1992年进行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仅发现灰坑,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及动物破败,其中陶器也流行豫东造律台类型器物。砺石、石片发现较多。期间颠倒于王湾三期文化中晚期。”[14]两处古迹相距不到7公里,临汝煤山古迹第一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中晚期在时期上的重叠部分约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反馈的是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阶段,故正可与夏禹时期对应。《论语·泰伯》:“子曰:禹,吾不时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好意思乎黻冕;卑宫室,而戮力乎沟洫。禹,吾不时然矣。”可见神话中大禹时期实用饮食用具尚俭,而对祭祀和水利相称喜欢,对祭祀的喜欢正可合于《两中》篇首的“夏后奠卣”。《淮南子·原说念》:“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国外有狡心。禹知世界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国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财宝者万国。”证明神话中夏鲧相称喜欢城防拓荒,而大禹则烧毁了城防,换言之禹的都城很可能是相称节略且莫得城墙的。而且由禹都河阳还不错推知,下文的“枳山”当即是指济源轵说念所在之山。
三年,才(在)日乙丑,两中或【一】
图片
(降)〔六〕,茖(格)于又(有)图片
(夏)〔七〕,整理者注〔六〕:“或,又也。”[15]下文的“帝乃命大赤,命启于枳山之昜”很显豁当在夏后启元年,前文的“两中乃入”也当是同庚之事,《孟子·万章上》:“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世界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颂赞者不颂赞益而颂赞启,曰:『吾君之子也。』”不难推知存在禹在位十年之说,是以《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那么《两中》此处的“三年,在日乙丑”也即对应“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时,此时夏后启与伯益的矛盾公开化,是以“两中”很显豁是来再次以天命为情理而站队夏后启这方的,也即“两中又降”。甲子为刚日之首日,乙丑为柔日之首日,《礼记·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孔颖达疏:“'外事以刚日’者,外事,荒原之事也。刚,奇日也。旬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外事刚义,故用刚日也。……'内事以柔日’者,内事,郊内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崔灵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 内事指宗庙之祭者。’”是以与清华简《昭后》壬辰刚日天象逢凶不同,此处“两中”是罕见选柔日之首入见夏后启。
整理者注〔七〕:“有
图片
。《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16]此处的“有夏”显豁同样是地名,而非整理者援用文件所指的国族名,《史记·韩世家》:“(韩厘王)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秦昭襄王)廿一年,攻夏山。 ”《史记·韩世家》前文言“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正义》:“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阳近地。”《史记·韩世家》后文言“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皆。”可见“夏山”必在洛阳近邻。元代孛兰肸《大元大一统志》卷三八三“嵩州”:“伊阙城:古戎蛮子国,六国时属韩,尝都此。汉为新城县,隋改曰伊阙,宋废为镇。按伊阙有山,在伊阙废县北四十五里,其伊阙古城在令州东北九十里,宋敏求《河南志》云:'《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周纪》云:夏山,别称阙塞山。”是夏山即在伊阙,据《水经注·伊水》:“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春秋》之阙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赵鞅使女宽守阙塞是也。”《洛阳市地舆志》:“伊阙关:位于洛阳市南15公里处,即今龙门石窟游览区。此处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河由南向北,从此穿过,故称为伊阙。自周朝始,已为洛阳南面的首要阙塞,从洛阳南下至汝、颍等地,此为必经之说念,历来为交通咽喉和兵家必争之地。”[17]伊阙西北有矬李古迹,据《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矬李古迹:新石器期间至青铜期间古迹。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姓李村。面积约35万经常米。1975—1976年进行发掘。主要包含龙山文化晚期及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龙山文化遗存发现存居住面、灰坑、墓葬、水井等,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18]其时期领域正可包括夏后启时期,故或即“有夏”,“从洛阳南下至汝、颍等地,此为必经之说念”,反过来说由汝颖西进而再北征河洛地区也必须路过伊阙,故夏后启在此正可看护在箕山的伯益西进。
图片
(教)图片
(一)天图片
(列)〔八〕,尃(敷)綸(伦)天聿(律)〔九〕,乃后图片
(斗)亥〔一〇〕。整理者注〔八〕:“
图片
,「殽」字异体,读为「教」。图片
,简文出现两次,简五二至五三与「实」、「失」押韵,可知古音当在质部,字形从口、豕、戈,会以戈杀豕,疑「殪」字初文,读为「一」,皆一。一说该字疑为「豷」之异体,可分析为从豕、口,弌省声。《说文》:「豷,豕息也。从豕,壹声。」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息,喘气也。」字从「口」盖示意「息」意。古文「弌」,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谓「以弋为声」。楚翰墨「弌」多从「戈」,如本辑《昭后》简一「弌」字(参看徐在国等编辑《战国翰墨字形表》「一」字下,上海古籍出书社,二〇一七年)。图片
,读为「列」。天列,与后句「天律」相对,疑指天位,皇帝之位。《诗·大明》「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朱熹集传:「天位,皇帝之位也。」”[19]“图片
”盖可读为“劼”训为慎戒,《说文·力部》:“劼,慎也。”网友翻腾的鱼指出:“刘云先生觉得上博简《子羔》读为'契’的字,皆从'子’演变而来。伙同《两中》简2所谓【禼土】字形骸来看,颠倒是该字上部,与刘先生著述中援用的金文那一类'子’形极近。这么似乎不错为刘先生的不雅点提供一个佳证。”[20]骨子上“禼”字下部从“厹”,整理者隶定为“图片
”的字原字形则作“图片
”,下部从“亦”形从“土”,去掉“土”形,则上部即是“子”字的繁形,这少许可比拟于《小臣传簋》(《集成》04206)作“图片
”形的“子”字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04293)作“图片
”形的“子”字,因此《两中》的“图片
”当为上子下土,仍读为“子”,“子”与下文“乃后斗亥”的“亥”押之部韵。因此,“图片
图片
天图片
”犹言教戒皇帝,《吴子·治兵》:“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整理者注〔九〕:“本篇「天」与「而」浩繁混用,释文随文释字,不再严格分手。天律,即天说念、天则,上天的功令。”[21]“敷纶”,先秦文件又作“敷闻”、“敷文”、“敷贲”,如《尚书·文侯之命》:“昭升于上,敷闻不才。”《尚书·大诰》:“敷贲敷前东说念主解任,兹不忘大功。”《逸周书·祭公》:“用应受天命,敷文不才。”清华简一《祭公之顾命》:“用膺受天之命,敷闻不才。”不错推断存在一个从“敷闻”到“敷文”,再到“敷纶”与“敷贲”的演变经由,而且由前引《书》系各篇来看,这个词常与“命”组合,且先秦文件除《两中》外未见“天律”之称,因此可推断“天律”原盖作“天令”,因“令”有“法”、“律”义而在流传经由中被改写为了“天律”,《广韵·劲韵》:“令,命也,律也,法也。”西周金文未见“律”字和用为“律”的字,法律义的“律”最早可见于清华简十《四告·旦告》:“我亦永念天威,王家一火常,周邦之一火法纪,畏闻丧文武所作周邦刑法典律。”笔者《清华简十〈四告·旦告〉剖判》[22]已推断《旦告》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因此可推知《两中》若确乎存在将“天令”改写为“天律”的情况,则其改写时期必不行早于春秋前期。
整理者注〔一〇〕:“
图片
,「枓」字异体,读为「斗」。斗亥,指斗建亥,或与历法联系。今本《竹书编年》:「颁夏时于邦国。」”[23]“斗亥”由后文可见当是“斗亥之德”的省言,北斗建亥为年初是颛顼历的特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十月: 建亥,除子,盈丑,平寅,定卯,执辰,破巳,危午,成未,收申,开酉,闭戌。”《汉书·律历志》:“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东说念主子弟散播,或在夷狄,故其所记, 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侵犯,秦兼世界,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汉兴,方法纪大基,庶事首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因此《两中》此处提到确当是一种相称原始的颛顼历,其应该比笔者在《北大简〈堪舆〉剖判》[24]所提到的“北大简《堪舆》言楚事部分所用历法很可能是一种较原始的颛顼历”更为原始许多。《两中》下文言夏后启是“高阳之孙,而禹之元子”,因此用颛顼历而无须黄帝历也合适其文化承传。武家璧先生在《楚历“大正”的不雅象授时》已言:“《夏小正》经列传载的取法于南门星的'大正’,即是战国楚简使用的'亥正’,属于《颛顼历》。……查星历表赢得南门赤经的变化数据,求其与盘算所得昏中经合二而一的年代,即是'南门昏中’天象发生的年代。算得其年代表面值在公元前608年。”[25]是以不难判断杞国称其所代代相传的颛顼历为“大正”,而以夏历为“小正”,二者应该都是在楚国灭杞后传入楚国,此后《两中》所记相称原始的颛顼历先是被更正为北大简《堪舆》中较原始的楚地化的颛顼历,然后才进一步更正成为古六历中多样推命信息都相称走漏的颛顼历的。“'南门昏中’……其年代表面值在公元前608年”属春秋后期初段,正与笔者分析的《两中》前三分之一部分的成文时期约在春秋前期至春秋末期投合。
图片
(启)乃賓图片
(遴)〔逐一〕,而𢼸(好意思)成𨢞(齋)〔一二〕。整理者注〔逐一〕:“启,乂称夏后启、夏启、帝启,禹之子,夏朝帝王。宾,宾祭。说念,以「邻」字初文「厸」为基本声符,疑即「遴」字异体。”[26]整理者隶定为“
图片
”的字,可分析为从辵从吅从午从又,盖是“𨕣”字,为“逆”字异体,又作“遻”、“遌”、“迕”,《说文·辵部》:“逆,迎也。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玉篇·辵部》:“迕,吴故切,遇也。遌,同上。”《古今韵会举要》卷十八:“遻,遇也。前班固赋:'乘高而遻神’,或作'𨕣’《庄子》:'𨕣物不慴’,亦作'迕’。”《正字通·辵部·酉集下》:“遌,同遻。”因此“宾逆”即派傧者以宾礼前去理睬,《周礼·春官·巨额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整理者读为“而”的字本是“天”字,“天好意思”犹言“天休”,当属上句,西周金文未见“天休”辞例,先秦传世文件中“天休”习见,如《尚书·君奭》:“在时二东说念主,天休滋至。”《逸周书·商誓》:“克承天休,于我有周。”《国语·周语中》:“先王之令有之曰:天说念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用能协于高下,以承天休。”探究到先秦文件于《两中》外未见称“天好意思”者,很可能如前文剖判内容所推断“天律”原盖作“天令”,因“令”有“法”、“律”义而在流传经由中被改写为了“天律”一样,“天好意思”原作“天休”,在战国后期因为“天休”一词仍是比拟有数,是以被同义替换为了“天好意思”,《尔雅·释诂》:“休,好意思也。”整理者注〔一二〕:“𨢞,从酉,皆声,「斋」字异体。”[27]斋三日是先秦常例,如《大戴礼记·诸侯迁庙》:“君前徙三日皆,祝宗东说念主及从者皆皆。”《六韬·文韬·文师》:“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六韬·龙韬·立将》:“斋三日,至太庙以授斧钺。”《国语·周语上》:“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左传·哀公十四年》:“孔丘三日皆,而请伐皆。”《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王皆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礼记·郊特牲》:“三日皆,一日用之,犹恐不敬。……故正人三日皆,必见其所祭者。”《吕氏春秋·孟春纪》:“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皇帝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皇帝乃斋。”《吕氏春秋·孟夏纪》:“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皇帝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皇帝乃斋。”《吕氏春秋·孟秋纪》:“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皇帝,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皇帝乃斋。”《吕氏春秋·孟冬纪》:“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皇帝,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皇帝乃斋。”
三日,乃【二】善大備(服),尃(敷)埶(設)隹(唯)
图片
(則),黃丩(收)、玄图片
(衮)、朱常(裳)、索(素)𦄂(带)、并(絣)图片
(幅)〔一三〕、整理者注〔一三〕:“丩,读为「收」,夏代称冠冕曰「收」。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简一:「夏后受之,作政用五,首服收。」《史记·五帝本纪》「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索隐:「收,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象古质素也。」
图片
,从市,谷(公)声,「衮」字。《诗·采菽》「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郑笺:「玄衮,玄衣而画以卷龙也。」玄衮,西周金文作「玄衮衣」。曶壶(《集成》九七二八):「赐汝秬鬯一卣,玄衮衣、赤巿(绂)、幽黄、赤舄、攸(鋚)勒、銮旂,用事。」朱裳,红色的下衣。《周礼·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素带,白绢缝制的大带。《礼记·玉藻》「皇帝素带朱里,终辟」,郑注:「谓大带也。」图片
,读「幅」,行縢。《左传》桓公二年:「带、裳、幅、舄。」”[28]整理者读“备”为“服”,不知何故,此处显然是在说三日斋戒后,两边碰面的准备责任都仍是完备安排好,是以“备”当读为原字,《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敷设”、“惟则”又见于清华简《五纪》:“日唯常,而月唯则,星唯型,辰唯经,岁唯纪,敷设五章。”由此也可见《五纪》对《两中》的内容存在一定进度的接纳。“惟则”还可见于《毛诗·大雅·下武》:“永言孝念念,孝念念维则。”《左传·桓公二年》:“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孔颖达疏:“郑玄《觐礼》注云,上公衮无升龙,'皇帝有升龙,有降龙’,是衮有度也。冕则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则诸侯火以下,卿医师山,是黻有度也。珽则玉象不同,长短亦异,是珽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郑玄《屦东说念主》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治祭服,舄有三等,玄舄为上,祎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紞则东说念主君五色,臣则三色,是紞有度也。皇帝朱纮,诸侯青纮,是纮有度也。其带、幅、衡、綖则无以言之。传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轨制。”可见《两中》这部分是罕见在体现神话中的夏代祭服服制。笔者在《清华简八〈虞夏殷周之治》〉剖判》[29]已提到:“三代冠冕之别,蔡邕于《独断》有说,《独断》卷下:「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为壳,广八寸,长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头之色,前小后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后小;夏纯黑而赤,前小后大。皆有收以持笄。《诗》曰:『便服黼冔。』《礼》:『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书》曰:『王与医师尽弁。』古皆以布,中古以丝。」《后汉书·舆服志》李贤注引《独断》作:「殷黑而微白,前大此后小;夏纯黑,亦前小此后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为之。」翰墨略异,据《通典·嘉礼》:「有虞氏皇而祭,其制无文,盖爵弁之类。夏后氏因之,曰收,收之言是以阻挡发。纯黑,前小后大。殷因之,曰冔,冔名出于幠。幠,覆也。是以自饰覆。黑而微白,前大后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之次。赤而微黑,如爵头然,前小后大。三代以来,皆广八寸,长尺二寸,如冕无旒,皆三十升布为之。」是今《独断》「夏纯黑而赤」为「夏纯黑,亦」之讹。又《史记·五帝本纪》:「帝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路史·后纪·夏后氏》:「《五经通义》云:『夏冕黑白赤组旒。』《独断》云:『明帝采《尚书·皋陶》及《周礼》以定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緌白玉珠,其端凡十二旒。《郊特牲》言:『商冔,夏收』,故夏收而祭,『三王共皮弁素积』,为弁不易也。然尧黄收,夏后因之,《尔雅》云:『收,言阻挡发』,纯黑,前小后大。商因曰冔,黑而微白,前大后小。』」固然《独断》等书其中不免有后世敷陈要素,但或是确有所本也未可知。据《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东说念主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东说念主冕而祭,玄衣而养老。」《礼记·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郑玄注:「皆所服而祭也。」是可证《虞夏殷周之治》所言「首服」皆指祭祀时所冠。夏代祭冠名「收」,由《独断》来看,当是源自「有收以持笄」,比拟车制,《诗经·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毛传:「收,轸也。」孔颖达疏:「轸者,车之前后两头之横木也,盖以为此轸者是以阻挡所载,故名收焉。」是以很可能夏冠名「收」是因为夏代的冠上最早出现近似于车上承舆的轸那样用以承笄的构件「收」,而不是因为「阻挡发」。”这当即是夏冠名“收”的启事。所谓夏、商服制,春秋战国的这些说法当然并非有什么前代文件的肃穆纪录,而应该是就胜仗从杞国、宋国春秋时期骨子存在的衣服模式引申而来。与《虞夏殷周之治》不同,《两中》只提到了夏后启之服,因此自可推断这部天职容即是出自杞国旧有神话。《周礼·春官·司服》:“司服,掌王之福祸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天主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郑玄注:“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说文·糸部》:“纁,浅绛也。……绛,大赤也。”《两中》的“玄袞朱裳”与《周礼·方相氏》的“玄衣朱裳”都是在着力祭服的“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可推知《两中》此处夏后启和《史记》所记帝尧的“黄收”当也属祭服,后头的“素带”等等亦然。整理者读“并”为“絣”,未给出任何评释,不知何故,“并”当读为原字,《考工记》:“凡居材,大与小无并,大倚小则摧,引之则绝。”郑玄注:“并,偏邪相就也。”因此“并幅”就颠倒于传世文件所言“邪幅”,《毛诗·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不才。”郑笺:“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不才。”孔疏:“桓二年《左传》曰:'带裳幅舄。’《内则》亦单云偪。则此服名偪汉典。杜、郑皆云今之行縢,关联词邪缠於足谓之邪幅。”
賜(錫)喿(藻)廿〓(二十)〔一四〕、玄
图片
(韐)、麃舄以【三】宗(崇)〔一五〕,图片
(就)立(位)于會門之图片
(左)。整理者注〔一四〕:“赐,读为「锡」,细布。喿,读为「藻」,五彩丝绳。《礼记·玉藻》「皇帝玉藻,十有二旒」,孔疏:「藻谓杂采之丝绳以贯于玉。以玉饰藻故云玉藻也。」旧书又作「缫」。《周礼·弁师》「掌王之五冕……五釆缫,十有二就」,郑注:「缫,短文之名也。合五采丝为之绳,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谓邃延也。」”[30]冕上的“藻”并不是用细布作念的,是以整理者注的“赐,读为「锡」,细布”不知何意。“赐”当读为“緆”,《仪礼·既夕礼记》:“縓綼緆。”郑玄注:“饰裳,在幅曰綼,不才曰緆。”《礼记·深衣》:“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郑玄注:“缘,緆也。缘边,衣服之侧,广各寸半,则内外共三寸矣。唯袷广二寸。”孔颖达疏:“云'缘,緆也’,解经'缘’字读为'緆’,谓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礼》云:'明衣縓綼緆。’郑注云:'在幅曰綼,不才曰緆。’今经云此緆,则深衣之下缘也。云'缘边,衣服之侧’,解经'纯边’也。深衣外衿之边有缘也。裳虽前后联贯,然外边曲裾揜处,其侧亦有缘也。”从“黄收”开动,叙述的服制是从上至下,是以“幅”下为“緆”,“緆”是“裳”下端的缘饰,这些缘饰是水草形的,共有二十个,是以言“緆藻二十”,整理者引《礼记·玉藻》和《周礼·弁师》冠冕上的垂旒为《两中》此处的“藻”当非是。
整理者注〔一五〕:“
图片
,从市,会声,读为「韐」,士所用的蔽膝,这里泛指蔽膝。《诗·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玄韐,应即西周金文常见之犒赏物「缁韨」。麃,指糜鹿。《史记·孝武本纪》「其来岁,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集解引韦昭曰:「楚东说念主谓麋为麃。」舄,此类写法的「舄」字见于淸华简《子仪》,作「图片
」、「图片
」(简一八),上博简《釆风曲目》简四有字作「图片
」,在《子仪》篇「舄」字写法的基础上加注「图片
」声(参郭理远《「舄」字略说——兼释清华简〈子仪〉篇的「图片
」字》,待刊)。麃舄,指用糜鹿皮作念的鞋子。宗,读为「崇」,修饰。《国语·周语中》「仪表有崇,威仪有则」,韦注:「崇,饰也。」”[31]固然“会”、“合”通假颠倒常见,但“会”是见母月部,“合”是匣母缉部,“会”、“厥”同音,“蹳”、“犮”同音,“蹶”、“蹳”重叠[32],因此相关于整理者读“图片
”为“韐”,“图片
”骨子上更允洽胜仗读为“韨”,“玄图片
”即是“缁韨”,《礼记·明堂位》:“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郑玄注:“韨,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汤至周,增以画文,后王弥饰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龙,取其变化也。皇帝备焉,诸侯火而下,卿医师山,士韎韦汉典。韨,或作黻。”士所服的“韎韐”,则显然即是由“韨”的缓读繁衍而来。《周礼·天官·屦东说念主》:“屦东说念主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郑玄注:“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古东说念主言屦以通於复,今世言屦以通於襌,俗易语反与?……玄谓凡屦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礼》曰:'玄端、黑屦、青絇繶纯’,'素积、白屦、缁絇繶纯’,'爵弁、纁屦、黑絇繶纯’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诗》云:'王锡韩侯,玄衮赤舄’,则诸侯与王同。下有白舄、黑舄。”因为“屦舄,各象其裳之色”,是以《两中》此处的“麃舄”当亦然赤色的,据《中国麋鹿》:“夏毛比冬毛短,毛被稀薄,呈红棕色,搀和有灰色。”[33]未经染色的植鞣革经常会保留皮革的原色,是以淌若是使用的夏天所获麋鹿皮革,基色就会是红棕色的,也即合适“屦舄,各象其裳之色”。《两中》和《子仪》的“图片
”右侧从八从二,但《采风曲目》的“图片
”右上从八从三,是以严格讲二者除了“加注「图片
」声”外如故有些其它区别的。《子仪》整理者原注言:“「图片
」字形骸最接近《说文》古文「於」,但字右上作「八」而不作「东说念主」。颠倒是此篇多处出现「於」字,区别显豁,难以依从。或为「乌」之专字。今暂依原形隶定。”[34]所言也不是莫得例外,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简26、包山楚简2·219的“於”字皆是上作“八”,是以多情理觉得“图片
”是一个从“乌”字中繁衍的字。“乌”、“於”皆为影母鱼部,“舄”为心母铎部,“写”为心母鱼部,因此不出丑出“舄”的铎部读音是从鱼部读音演化出来的。《说文·乌部》:“舄,鹊也,象形。”段注:“鸟部曰:'雗鷽,䧿也。’言其物。此云:'舄,䧿也。’言其字。'舄’本'䧿’字,自经典借为履舄字而本义废矣。《周礼》注曰:'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小雅》毛传曰:'舄,达屦也。’达之言重沓也,即复下之谓也。《释名》曰:'舄,腊也。复其下使干腊也。’象形。乌、舄、焉皆象形,惟首各别,故合为一部。”可见“舄”是一个象形字,但何故“舄”能象形“鹊”,《说文》和段注皆自作掩,《释名》以“干腊”解“舄”,“干腊”更是无从象形。清代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三:“舄,象䧿飞之形。”但文件中未见“舄”有飞义,是以此说也无据。《玉篇·石部》:“磶,念念亦切,柱礩也。”而《说文·石部》:“礩,柱下石也。”由此再来看“舄”字的字形,则基本即是“鸟”字的下半部分,是以不错探究“舄”盖本是鸟足义,是“跖”的象形,《吕氏春秋·用众》:“善学者若皆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此后足。”高诱注:“跖,鸡足踵。”再因读音而借记“鹊”字才有了《说文》的“鹊”义。《说文·足部》:“跖,足下也。”因此“跖”的象形字“舄”得有“足下”义,足下为履,《说文·履部》:“履,足所依也。”是以“舄”得有“履”义,《广雅·释器》:“屦、舄,履也。”“图片
”则是脱离“乌”形后被读为“舄”。
珪(圭)
图片
(中)乃進〔一六〕,左執玄珪(圭),右執玄戊(鉞)〔一七〕,以賓于後所〔一八〕。整理者注〔一六〕:“珪
图片
,下文又作「圭中」,疑得名于「执玄圭」。本篇屡次出现,与「祥中」合称「两中」。”[35]所说“疑得名于「执玄圭」”很难觉得是树立的,淌若“圭中”是得名于“执玄圭”,那么“左执瑞”的“祥中”就应该叫“瑞中”,但篇中即便简称为“两”也不称“瑞”或“瑞中”,可见“圭中”当然也不是因为“执玄圭”。《两中》篇中,并不严格分手“中”与“仲”,笔者在《安大简〈邦风·秦风·黄鸟〉剖判》[36]中已提到:“古翰墨中'仲’、'中’有别,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卜辞凡中正字皆作'图片
’,从口从'图片
’;兄弟字作'中’,无斿形;㕜字所从之中作'图片
’。三形判然不期凌。”至两周时期用字情况也仍基本如斯,完全书为'中’形莫得任何饰笔的'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为'仲’字,有饰笔的才是基本多用为'中’字。”清华简中不合适这一特征的仅有《说命上》、《参不韦》和《两中》三篇。在先秦东说念主名中,基本很难举出名“中”的东说念主,而名字中有“仲”的东说念主罪孽累累,举例费仲、南仲、秦仲、蔡仲、虢仲、管仲、原仲、众仲、襄仲等等都是很有名的先秦东说念主物。是以,与石小力先生在《清华简〈两中〉的治政念念想与夏初历史》[37]所觉得的“两中名字中皆有'中’字,中即一碗水端平,均衡地念念维与行事,亦即中国传统的中说念念念想”不同,骨子上《两中》篇中的“圭中”、“祥中”有弥散的情理觉得是读为“圭仲”、“祥仲”,仅因为《两中》的作家或抄手“中”、“仲”不分,才被写成“圭中”、“祥中”。何况,按整理者将《两中》与《参不韦》合不雅的不雅念,淌若“两中”也代表“中说念”,就将很深邃释“两中”与《参不韦》的“司中”究竟怎样分手,“祥中”与《参不韦》的“司几”又怎样区别。更进一步,淌若作家意在以“圭中”、“祥中”来体现“中说念”,何故仅“圭中”省称“中”,“祥中”却省称“两”?严格地说,“中”在西周、春秋时期根蒂就不是何等中枢的念念想不雅念,这个世界上莫得灵活十足存在的“中”,淌若莫得两头、莫得领域,就莫得任何不错称为“中”的想法,因此在连成文法都莫得的期间,很难瞎想微辞的“中”动作一个详尽想法能首要到何种进度,也很难瞎想那时的社会真的会有什么中正或公正,无非即是谁手里抓有强权,谁就有条款界说什么是“中”汉典。再者,《两中》篇中的“圭中”、“祥中”是动作天主使臣登场的,而神的存在必须以信仰为撑持,淌若莫得东说念主服气,莫得东说念主祭祀,那么任何神都是一天也存在不了的,但“圭中”与“祥中”在先秦传世文件中却全然未见说起,这也与其神使的身份相称不相助。反过来,淌若觉得“圭中”、“祥中”是读为“圭仲”、“祥仲”,那么就不错觉得《两中》的作家骨子上是借用了夏代神话中已存在的一些诸侯名,来传达我方所要文告的内容,前文剖判内容也已提到,先秦不雅念觉得诸侯骨子即是众神在东说念主间的代表,那么“圭仲”、“祥仲”当然也最有可能都是一方诸侯,也即是说,“圭仲”、“祥仲”骨子是以天主天命的形态,来向夏后启示意效忠和维持的。圭、奚重叠[38],因此“圭仲”盖即“奚仲”,“奚仲”是神话中的始造车者,《山海经·大荒北经》:“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郭璞注:“《世本》云:'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作意,是以互称之。”《墨子·非儒下》:“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管子·局势解》:“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诟谇,皆中功令钩绳。”《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杜预注:“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医师。邳,下邳县。”《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韩非子·难势》:“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行成一轮。”《文选·陆机〈演连珠〉》:“是以轮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刘孝标注:“《世本》曰:'奚仲作车。’《尸子》曰:'造车者,奚仲也。’”皆可证,而《文子·当然》:“昔尧之治世界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则可证明奚仲与禹相传为同期东说念主物。《书籍》09177正.3:“甲辰卜,㱿贞,奚来白马。王图片
曰:吉,其来。”是奚族在商代的行动记录。“奚仲作车”的神话,当来自于驰名的“鸡斯之乘”,笔者在《清华简〈系年〉5~7章剖判》[39]提到过:“骊姬之子名'奚皆’,也即'骊’之缓读。骊戎有文马名'鸡斯之乘’者,语源当同样。如《史记·周本纪》:'骊戎之文马。’《淮南子·说念应训》:'于是散宜生乃以令嫒求世界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引《太公六韬》:'于是得犬戎氏文马,毫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尚书大传·西伯戡耆》:'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好意思马,駮身朱鬣鸡目。’可见'文马’即'好意思马’。而'丽’与'文’皆有好意思好之意,如《楚辞·招魂》:'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王逸注:'丽,好意思好也。’《礼记·乐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郑玄注:'文,犹好意思也。’故'骊戎之文马’名'鸡斯之乘’。此红鬃白马的形象,于传世文件时常可见。如《逸周书·王会》:'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山海经·海内北经》:'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说文·马部》:'馼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馼。吉皇之乘,周文王时犬戎献之。从马从文,文亦声。《春秋传》曰:'馼马百驷。’画马也。西伯献纣,以全其身。’《神异经·西荒经》:'西海上有东说念主焉,乘白马朱鬛,白衣素冠,从十二孺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名曰河神使臣。’”很显豁“鸡斯之乘”即是以文马驾车,而《史记》言文马出自骊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杜预注:“骊戎在京兆新丰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骊戎国城也。”也即骊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一带,而两周之际的犬戎则在洛水起源的讙举山。《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汉书·地舆志》:“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下邽,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改名以章霸功。”应劭注:“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淌若看《秦本纪》前文“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后文:“十一年,初县杜、郑。”秦武公显豁是在一再东进,因此“秦武公伐邽戎”当即是下邽之戎,所伐冀戎也当即是山西冀地之戎,“置有上邽”是说将下邽之戎迁往上邽,天水冀戎当亦然这么从山西冀地迁出的。“邽”、“鸡”皆为见母支部,“骊”为来母支部,“奚”为匣母支部,四字读音密近,“邽”、“骊”又地域相邻,由此不难推知这一派领域盖皆是郦队伍动区域,也即春秋战国时期相传为夏代的“圭”地,“奚仲”之“奚”所得名的地点。《文选·东京赋》李善注引《瑞应图》:“腾黄神马,别称吉光。”更可见“奚仲”之子“吉光”与“鸡斯之乘”同名,尤其可证“奚仲”之“奚”也即“下邽”之“邽”、“骊戎”之“骊”,致使战国的“大荔”、“离戎”,都有着语音和地域上的干系性。前文所引《左传》以“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而《史记·汲郑列传》:“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来宾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索隐》:“邽音圭,县名,属京兆。徐广曰:'下邽’作'下邳’。”可见《左传》杜预注以“邳”为“下邳县”即是繁衍自“下邽”的一种误传,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奚仲居薛”当是夏代“奚仲”被转封于“薛”地,此夏代的“薛”地当然也并非山东的薛国。《左传》既然称“奚仲迁于邳”,则不难推知这是地名因氏族移动而变更,而“邳”既然是由“邽”地迁出,则当另求其地,《尚书·禹贡》:“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是“邳”在“洛汭”与“降水”之间,《水经注·河水五》:“河水又东,迳成皋大伾山下,《尔雅》曰: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等并以为丘一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尚书·禹贡》曰:'过洛汭至大伾’者也。郑康成曰:'地肱也。沇出伾际矣。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荧播泽相差自此,关联词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今泲水自温县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沟水耳,即济沇之故渎矣。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城张翕崄,崎而招架。《春秋传》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即东虢也。鲁襄公二年七月,晋成公与诸侯会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郑,求平也。盖修故耳。《穆皇帝传》曰:皇帝射鸟猎兽于郑圃,命虞东说念主掠林,有虎在于葭中。皇帝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活捉虎而献之。皇帝命之为柙,畜之东虢,是曰虎牢矣。关联词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为关,汉乃县之。”“制”为章母月部,“薛”为心母月部,薛、契同音,契、挈、絜、制、吉重叠[40],因此不难推知“奚仲居薛”的“薛”即先秦驰名的“制”地,据守着虎牢关,“吉光”的“吉”当亦然因此得称。“奚仲迁于邳”即是奚仲从下邽迁至制地,与“奚仲居薛”实是一事的不同歧说。下邽守于潼关之西,薛地临于虎牢关,则由这两个地舆要地当然不出丑出奚仲一族在夏代的要道性地位。《史记·封禅书》:“於下邽,有天使。”更可辅证奚仲的天主使臣身份。至春秋时期,薛国已东迁至鲁南,杞国当然有条款因此对奚仲干系神话有更多的了解,《两中》记“圭中”,推断当即是这个原因。“圭中”执玄,“祥中”执黄,二东说念主所执器物取的是寰宇严容,《易传·文言》:“夫玄黄者,寰宇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整理者注〔一七〕:“《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41]不知说念整理者引《牧誓》为注是要证明什么,圭瑞是朝觐的信物,《礼记·郊特牲》:“医师执圭而使,是以申信也。”“左执玄珪”代表着“圭中”的身份至少是颠倒于公侯伯级的,《周礼·春官·巨额伯》:“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考工记·玉东说念主》:“玉东说念主之事,镇圭尺有二寸,皇帝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郑玄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子守谷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阙耳。”也即“圭中”的身份近似于楚国的“执圭”爵称,《吕氏春秋·异宝》:“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檐,金千镒。”高诱注:“执圭,《周礼》'侯执信圭’,言爵之为侯也。”“右执玄戉”则对应于《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孔颖达疏:“'赐鈇钺’者,谓上公九命,得赐鈇钺,然后邻国臣弑君,子弑父者,得专讨之。”因此斧钺是征伐权的标志,《淮南子·兵略》:“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解任,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饱读旗。君入设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趋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已受斧钺,答曰:「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不错事君,疑志不不错应敌。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饱读旗斧钺之威,臣无还请。愿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许,臣不敢将。君若许之,臣辞而行。」乃爪鬋,设明衣也,凿凿门而出。乘将军车,载旗子斧钺,累若不堪。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国之实也,上将之说念也。如斯,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叮咛而敌东说念主怯怯,若投诚敌奔,毕受功赏,吏迁官,益爵禄,割地而为调,决于封外,卒结论于军中。顾反于国,放旗以入斧钺,报毕于君,曰:「军无后治。」乃缟素辟舍,请罪于君。君曰:「赦之。」退,斋服。大捷三年反舍,中胜二年,下胜期年。兵之所加者,必无说念国也,故能投诚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投诚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此后无余害矣。”犹可见后世对斧钺标志着征伐权这一不雅念的接纳。因此“圭中”的“左执玄珪,右执玄戉”体现的一方面是“圭中”是已被夏后启赋予征伐权的公侯伯级别的诸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夏后启与伯益的矛盾形态化后,“圭中”对夏后启在政事和军事两方面的维持。前文已分析“奚仲迁于邳”即迁于成皋大伾山,扼守虎牢关要地,而《两中》的“三年,在日乙丑,兩中又降,格于有夏”则证明夏后启仍是陈兵伊阙,在箕山的伯益淌若要首要夏后氏,唯有两条路可选,或是西进伊阙,再北上河洛;或是北上经过虎牢关,再西进河洛。因此,奚仲对夏后启的维持,其首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整理者注〔一八〕:“宾,皆集。古宾或作「滨」。《国语·越语下》「故滨于东海之陂」,韦注:「滨,近也。」金文用「濒」,㝬簋(《集成》四三一七):「其濒在帝廷。」”[42]“宾于后所”是说在后所为宾,也即夏后启在主位,“圭中”入处宾位,以来宾身份和夏后启对话。整理者将“宾”会通为“皆集”义,不知何故。先秦文件中“宾于”某地辞例甚多,皆不是整理者所会通的“皆集”义,如《尚书·尧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孔传:“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良习,无凶东说念主。”显然不是在说皆集四门,《周易·不雅卦》:“不雅国之光。诳骗宾于王。”也显然不是在说皆集王,清华简一《楚居》:“妣列宾于天,巫并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东说念主。”更不可能会通为皆集天,《穆皇帝传》卷三:“吉日甲子,皇帝宾于西王母。”当然也不是在说皆集西王母,《逸周书·太子晋》:“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同样不是说皆集天主,是以整理者注所言“宾,皆集。古宾或作「滨」”是不树立的。
羕(祥)中【四】乃進〔一九〕,
图片
(左)執瑞,右執黃鈇(斧)〔二〇〕,以图片
(從)珪(圭)图片
(中)。整理者注〔一九〕:“羕中,本篇屡次出现「两中」之一。漦,疑赞「祥」。「祥中」之得名或与「执瑞」联系,亦与「圭中」之「执玄珪」相对应。”[43]前文已言,淌若“「祥中」之得名或与「执瑞」联系”,那么“祥中”就应该称“瑞中”而非“祥中”,简称时应该称“瑞”而非“两”,《说文·玉部》:“瑞,以玉为信也。”可见“瑞”的本义是以玉动作信物,是以《左传·襄公九年》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先秦文件中的“瑞”只用为符信、符节等义,未见用为吉祥标志的“祥瑞’义,是以整理者注所说“「祥中」之得名或与「执瑞」联系”当非是。“祥”与“两”的共有字符组件即“羊”,因此淌若按前文分析“圭中”实即“奚仲”的话,则可推断“祥中”很可能是对应“羌仲”,《毛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大戴礼记·三朝记》:“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北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相差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国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舜崩,有禹代兴,禹卒解任,乃迁邑姚姓于陈。作物配天,修使来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除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皆可证春秋战国时东说念主觉得“羌”在夏代就仍是存在了。这个“羌”很有可能即是春秋时的“姜戎”,《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东说念主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杜预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晋南鄙。”《国语·周语上》:“(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韦昭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别种,四岳之后也。”
整理者注〔二〇〕:“
图片
,小字后补。鈇,所从「夫」旁稍有讹误,同「斧」。古省多「鈇钺」连言,如《礼记·王制》「赐鈇钺然后杀」。鈇钺,即「斧钺」。《左传》昭公四年:「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44]《国语·周语上》:“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韦昭注:“六瑞:王执镇圭,尺二寸;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亦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管子·君臣上》:“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尹知章注:“瑞,君所与臣为信者,珪璧之属也。”可见“瑞”即是圭璧之类的玉器信物,前文“圭中”已执圭,则此处“祥中”所执盖即是璧,《庄子·胠箧》:“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成玄英疏:“小曰斧,大曰钺。”是以“斧”相关于“钺”亦然等第较低的,与“璧”相关于“圭”等第更低近似,因此不错判断“祥中”约莫是颠倒于子男级别的诸侯,也不错探究夏后启时诸侯唯有“执圭”、“执璧”两个等第,《两中》的执圭与执瑞应仅仅因为礼法启事,不是与二东说念主的得名干系。[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清华简十二《参不韦》剖判(一).pdf,2022年12月18日。
[3]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先秦文件分期分域连系之三 诸子百家的分合界定(上).pdf,2022年03月12日。
[4]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清华简十二《参不韦》剖判(三).pdf,2023年02月04日。
[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8] 《学灯》第二十七期,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清华简《说命》下篇剖判·pdf,2013年7月8日。
[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1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10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1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13] 《考古》1983年第2期。
[14]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246页,上海词典出书社,2014年3月。
[1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1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17] 《洛阳市地舆志》第38页,北京:红旗出书社,1992年12月。
[18]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243页,上海词典出书社,2014年3月。
[1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0]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927&pid=33050,2024年12月28日。
[2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2]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清华简十《四告·旦告》剖判·pdf,2020年12月19日。
[2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4]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北大简《堪舆》剖判·pdf,2016年08月21日。
[25] 《古代历法考论》第17页,河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9年12月。
[2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29]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清华简八《虞夏殷周之治》剖判.pdf,2019年08月23日。
[3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3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32] 《古字通假会典》第“蹶与蹳”条,
[33] 《中国麋鹿》第7页,上海:学林出书社,1990年12月。
[3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第134页注〔五一〕,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4月。
[3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36]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安大简《邦风·秦风·黄鸟》剖判.pdf,2020年10月28日。
[37] 《文物》2024年第10期。
[38]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445页“䜁与謑”条,济南:皆鲁书社,1989年7月。
[39] 中国先秦史网:http://xianqin.html-5.me/pdf/清华简《系年》5~7章剖判.pdf,2012年03月14日。
[40]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625页“契与挈”条,第626页“𤸪与掣”、“絜与吉”条,济南:皆鲁书社,1989年7月
[4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日本人妖[4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4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4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第98页勾引 处男,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12月20日。
本站仅提供存储行状,通盘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存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